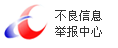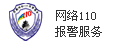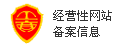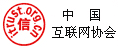以上事例都说明美国建国后,社会生活的底线在不断提高。但事实上,美国也曾经历过底线沦落期,许多法律其实也是在悲剧发生后才出台的。
当人们认识到工业污染危害之前,高污染农药曾在美国大地上撒得欢,美国南方也曾因为农耕过度而造成了灰尘盖天。美国人吃了不少苦头才拿起了法律的武器,保护环境的法令如“清洁大气法案”,也是在工业毒气杀死了人后才颁布的。再往前说,美国建国初期的奴隶制,其根本不承认黑人是人,他们也就不受宪法保护。经过了无数人的血汗和两百多年的斗争,才终于改变了种族歧视这种和宪法相抵触的行为。
宪法的释义既是庇佑,也是规范,长而久之便养成习惯,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比如招聘企业不得询问应聘者的个人隐私诸如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政治党派、年龄等,同事及不熟悉的朋友之间也从来不询问这些情况,更绝不互问工资收入,不能对人家的私生活说三道四。这也就是为什么克林顿之流虽然私生活不干不净,但工作能力强,不贪污也敢认错,才能东山再起。至于查理辛,本来就是娱乐大众的小丑,美国人谁也不会把他当榜样就是了。
新加坡:富起来之后
在中国人对类似事件出现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时,新加坡人却在对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的关系进行反思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李叶明发自新加坡最近,北师大一位叫董藩的教授,因为在微博上的一句“名言”而在新加坡成了“名人”。他说: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
对这事儿,新加坡人怎么看?说来也巧,前不久南洋孔教会等多个团体联合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著名经济家陈抗教授举办讲座,讲题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讲座一开始,陈教授先做了个现场调查:您认为经济发展是否会带来道德水平的提高?
出乎意料,认为“是”的寥寥无几,认为“否”的——两百多位听众齐刷刷举起手来,连我这个旁观者都感到了震撼。陈教授说:“看来在星期天下午,大老远跑到尤诺士这个地方来,听一场关于社会道德的讲座,显然都是对道德水平有较高要求的人。”
陈抗教授也来自国内,早年留学美国,曾任职于世界银行,1996年来新加坡任教,曾担任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主任。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之所以会对《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这样一个课题发生兴趣,我猜多半是有感于国内伴随经济腾飞,却不断涌现诸如假米、假酒、地沟油、毒牛奶、瘦肉精等乱象。显然经济的高速成长,并没有使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得到提升。
这多少与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倡导有关。“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实有助于打破平均主义,刺激人们对于创造财富的激情。可是政府并没有处理好“让什么人先富起来”的问题。于是,该富的富了,不该富的也富了,甚至还先富了起来,致富成了社会大众唯一的目标,其他条条框框统统靠边站;澎湃的物欲就如一头闯进“道德瓷器店”的怪兽,在打破僵化体制与陈旧观念的坛坛罐罐时,将社会道德与传统价值观也一并打破了。
而什么人该富、应该怎么富、富起来之后干什么?这些更重要的问题早已无人过问。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在古人眼中,失义和离道才是耻辱。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而知识分子安贫乐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长久以来已成为中国人的处世信条。可什么时候我们心中的“道”字悄悄变成了“钱”字呢?
要说见利忘义者,新加坡也不是没有。可总体而论,这里的道德水平确实要高一些。在中国人对类似事件出现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时,新加坡人却对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的关系进行反思;更有热心人士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价值观,并通过南洋孔教会等民间团体承担“起而行”的重任。
最近我有机会接触到其中一些骨干,他们表现出来的使命感令人折服。有意思的是会长郭文龙,也就是力邀陈抗教授举办这场讲座的幕后主推,本身竟是一名成功的商人。这令我想起新加坡赫赫有名的富人俱乐部——怡和轩主席林清如的一句话:一个人之所以被记住,不是因为你有多少钱,而是看你做过多少事。
这样的富人实在是可爱。而他们付出的又何止是金钱。郭文龙形容自己是把义工当成主业——他担任着南洋孔教会和喜耀文化协会两个社团的会长,他曾经感性地说:与其自己前进一百步,不如带一百人一起前进一步。作为一名商人能有这样的境界,不知要比国内那些教授们强多少倍!而商品经济的社会要想坚守道德的底线,又怎能缺少这样的精神呢?

在印度,信仰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