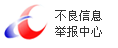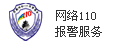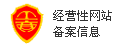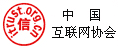在卢新死后第二日,富士康将多名中国最好的心理学专家请到厂区,寻求强有力的心理学支持。但仍无济于事,员工祝晨明又跳楼。之后,富士康请了五台山最有名的高僧大德,到园区为死者祈福。
在“六连跳”到“七连跳”、“八连跳”,有媒体质疑连续出现的自杀事件,是因为富士康是“血汗工厂”,高密度的死亡与其“半军事化管理”有关。
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副主席陈宏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第六跳”发生后第二天,深圳市总工会便到富士康调查。4月13日下午,深圳市总工会公布富士康近期多位员工坠楼事件的调查结果。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称:富士康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希望企业吸取教训,建立人文关怀的管理体制。
“群体这么大,基层的管理上肯定会有些做得不好的地方,但这和自杀肯定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陈宏方说。
南方周末在富士康的近一个月调查发现,管理本身并无异常之处。
“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也很难与富士康的工作压力、‘血汗工厂’联系起来。”北师大心理学教授张西超说,“当然,我们也认为,富士康应加强对员工的心理危机干预,防止类似悲剧发生。”参与调研的心理学家均认为,这些自杀事件基本与富士康员工个人的心理疾病,特别是抑郁症有关。
据富士康集团行政总经理李金明介绍,实际上早在2009年7月份的孙丹勇事件后,员工的心理健康便出现在富士康(中国总部)最高管理层的问题单上。一批心理咨询师补充到了集团里来。
现在,富士康还开通了78585(谐音“请帮我帮我”)热线电话,给员工提供心理咨询。与此同时,一个旨在疏解员工心理压力的“心灵港湾工作室”也开设了,员工在这里不仅可以接受心理辅导、通过专业仪器放松身心,还可以在确保隐私的前提下,在宣泄室击打橡皮假人。
“公司管理层都愿意把自己的照片,套在假人上,供员工们发泄。”刘坤说。
4月下旬,针对员工之间缺少沟通的现象,为了方便室友之间交流,富士康甚至下通知鼓励朋友、老乡住在一个寝室。“我们在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即兴搞过有奖问答,谁能说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奖励1000元。但绝大部分人答不上来。”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说。
刘坤告诉记者,郭台铭将在本周内专程赶赴深圳,为“员工关爱中心”挂牌。成立的日子还不到20天,悲剧再次发生了。
新一代打工者普遍性的焦虑
“许多问题,都出在上游,只是因为水流到了富士康这里,问题集中暴露出来,所以大家以为是富士康的问题。”刘坤认为。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曾经多年研究过深圳的农民工问题。在他看来,“八连跳”并不仅是富士康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心理问题,更是社会的问题。“只是因为富士康人口基数大。”刘开明说。
刘开明在整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群体的历史中,研究当前农民工高密度自杀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在全民普遍低薪的历史背景下,农民工(外来工)的工资每月高达200—600元,当时大学教授的月工资只有180元左右。而在1992年之后,得到制度庇护的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增长迅速,但遭遇制度性排斥的外来工工资增长则十分缓慢。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2008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出口工厂的工人平均年收入仅是这两个地区城镇在岗职工年均工资的37.82%。
“考虑到CPI的因素,新一代的打工者,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所获得的薪酬,要远远少于第一代打工者。”刘开明说。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潘毅,早在1990年代后期,便开始关注中国的打工群体。她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新生代打工者相对他们前辈,承受着更多的焦虑。
从2005年到2008年间,潘毅多次和同事在深圳和东莞,研究新生代打工者,她得出的结论是,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家乡回不去了。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不会从事农业生产、不适应农村生活;二则,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即使想回去,家里也没有土地。
实际收入锐减,退路又无,新一代打工者面临着比他们的前辈更大的生存压力。
而涂尔干所谓遏制自杀的最有效的障碍——集体,也并不能给中国的新生代打工者提供帮助。
“目前的社会管理制度框架,使每一个打工者处于原子状态,他们没有自我救助与沟通的组织。”刘开明说。
富士康行政总经理李金明以他的方式描述了工人的这种“原子”状态:“不管是正式组织,比如工会,还是非正式组织,比如老乡会,同学会,普通员工都找不到,所以压力大,却无法舒缓。”
“必须从源头解决问题,一方面,提高打工者的收入,消除他们的集体焦虑感;建立有效的集体组织,让他们处于一个多维度的人际关系网中。”刘开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