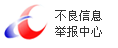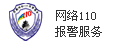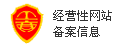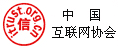“进去以后,我们就是呆在行政楼大厅或办公室里,等领导来。”张树民说。
被闹得焦头烂额的陡河发电厂让步了:请专业队伍鉴定李家峪、韩家哨、甘雨沟等村的房屋受损情况,酌情补偿;从2006年到2012年,给李家峪灰场周边14个村的村民发放飞灰污染费,头3年每人每年500元,以后逐年递减。
“为了这些事,我们村干部去交涉过无数次,一直不给解决。一大帮老百姓去上几回,很快就有眉目。”宋家峪村村主任朱会荣说。
房屋受损鉴定结果出来后,陡河发电厂陆续拿出赔偿方案:韩家哨800万元;李家峪7500万元,就地翻建……
甘雨沟村在2007年1月得到了30万元,但陡河发电厂方面并不承认该村房屋开裂与李家峪灰场有关,“通过专家观察,从裂纹形态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老化失修造成。”
“攀比”
负责人王晓静说,因受损程度、历史原因等不同,各村所得赔偿不等,但村民就是要向高的看齐
兑现赔偿承诺后,能否就此了断与村民的纠纷,陡河发电厂并不乐观。
陡河电厂专门负责解决厂村矛盾的王晓静说,灰场渗水和飞灰给村民造成的损失,有些已经补偿过,白纸黑字还有红手印,但村民不管这些,还是来索赔,张树民即是其中之一。
对甘雨沟的30万元赔偿,协议是陡河发电厂和甘雨沟村委会之间签订的,当时张树民是村主任。其中明确写道,赔款用于弥补村民房屋、果窖、薯井、地上建筑物因灰场而受到的经济损失,赔款到位后,村民不得以上述事项为由再次索赔。
甘雨沟村委会把钱分成若干份发给村民时,双方也签订了协议,内容仅仅是分配方案,没有提及赔款事由,更未附加其他条件。
领钱时,村民们只知道这是陡河发电厂给的,并不清楚具体名目。张树民的邻居朱凤莲说,她压根就没见过协议书。
左手刚把钱装进兜里,右手就推门直奔陡河发电厂,包括张树民在内的甘雨沟人今年1月又上门索赔,这次要求是:赔偿2005年之前的污染费,赔偿因果窖和薯井损坏导致水果和白薯贱卖甚至无法种植而遭受的损失,就地翻建或者整体搬迁。
“我们村的受损程度不比李家峪轻,为什么给他们翻建,不给我们翻建?”张树民说,陡河发电厂是央企,每年赚很多很多钱,如果它穷得叮当响,谁还会去索赔。
坊间传言又将得到巨额赔偿的宋家峪,也感到委屈。村主任朱会荣说,这两年,陡河发电厂花费几百万元给李家峪和韩家哨打深井,夹在这两个村当中的宋家峪,为什么被漏掉?
“相互攀比。”王晓静说,因为受损程度、历史原因等不同,各村所得赔偿多少不等,有的几十万,有的几百万。但村民不管什么理由,就是要向高的看齐,连锁反应,没完没了。拿到巨额赔款的,也屡生事端,“就在前几天,李家峪把我们的车又拦了。”
言语间,陡河发电厂方面还透露了另一层意思:周围村民对电厂的要求已经超出正常维权的范围。该厂一名戴姓负责人说,灰场种树,雇外面人,一棵8毛,但有村民不许电厂把活给别人,只能以一棵1.2元的价格让他们干,否则就搞破坏。
迟到的环保
2007年起发电厂投重金治理。“从去年开始,粉煤灰少多了,渗水也轻多了。”朱会荣觉得变化挺大
灰场周边村民连年索赔,不可否认的一个原因是,灰场治理姗姗来迟。
为抑制飞灰,陡河发电厂作出过种种努力:改变3个排灰口的位置,尽量沿灰场周边多口、轮流、倒换排灰,将灰水赶到灰场的中间地带,使灰水覆盖灰场大部分灰面,保持湿润,防止扬尘;安装喷淋设施;将整个灰场分成三大格,分期覆土;在靠近陡河水库的灰场西侧种植美国红柳;将水力除灰部分改为气力除灰,即干除灰,将灰简单处理后卖掉。
这些工作从1998年陆续展开,但直到2007年,绿化面积不到灰场灰面的1/10,陡河发电厂半数机组仍用水力除灰。
村民闹得最凶的2006年、2007年,正是李家峪灰场渗水、飞灰最厉害的时期,灰面面积达250万平方米,灰面标高80多米。
北京奥运会的到来,使李家峪灰场的治理速度猛然提到“动车级”。2007年,陡河发电厂倾囊而出搞环保,当年的“三大工程”中,有两大工程是为了粉煤灰治理。其一,改造除灰系统,所有机组均用气力除灰,同时进行湿渣脱水改造,把煤渣加工成煤灰卖掉,设备正常运转时,不再向李家峪灰场排灰,那里只作为事故备用灰场;其二,治理李家峪灰场,全面覆土、绿化,种上美国红柳、扶芳藤、沙棘等。
陡河发电厂的一份汇报材料显示,北京奥运会开幕前,灰场治理工作全面结束,剩下的就是后期管理,以及对没有成活的树木进行补种。电厂负责人郑刚说,现在有20来人专门负责灰场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