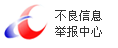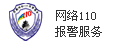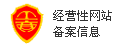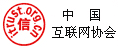渗水导致的另一大问题是,地基下沉,房屋开裂。当时李家峪村300来户人家,有60来户的房屋开裂严重。时任村主任的侯长江说,大概是从2000年起,陡河发电厂以多种名目补助该村,如建房费、过冬费、污染费。
灰场西北角的宋家峪村,原本窝在山凹中,由于渗水厉害,1990年不得不集体挪动100多米,移到山包上。在该村村主任朱会荣记忆中,那时候,原本一直干涸的山沟,积水1米多深,各家各户的房子或大或小都裂缝,地面总是湿漉漉的。那次,陡河发电厂给了1500万元。
与此同时,灰场北侧的韩家哨村,部分房屋出现类似症状,陡河发电厂又拿出300万元予以补偿。前任村主任韩泽廷说,政府本来答应另给300万,但最后有130万没兑现。
灰场周围的村庄,陆续找上陡河发电厂的门,以同样的理由索赔。
飞灰
为遏制渗水而实施的高浓度除灰,却隐藏另一祸端。大风经过,粉煤灰翻山越坝,飞向村庄
陡河发电厂忙于遏制李家峪灰场渗水时,另一祸端悄然长成、肆虐,这就是飞灰。
为从源头上掐断灰水,1992年,陡河发电厂改造除灰系统,将灰水比例骤变为1:5左右,高浓度除灰。
灰水浓度提高、实现厂内循环污水后,灰场积水迅速减少,露出一片一片的灰白色。大风经过,裹挟着细小而轻盈的粉煤灰翻山越坝,飞向甘家沟、李家峪、宋家峪、韩家哨等。漫天飘舞的粉煤灰钻过窗缝落在炕上、柜子上,铺下一层厚厚的灰白色。
在张树民印象中,飞灰成灾开始于90年代中期,“好家伙,像下雾一样,大风起大雾,小风起小雾。”
大风呼呼,树枝抖动着弯腰低头,整个村子被白色笼罩。一段拍摄于2004年5月份的录像,佐证着张树民的说法。
位于灰场东南角的甘雨沟,原本以种植白薯为主,每到秋季,家家户户房顶上晒白薯干。张树民说,飞灰越来越多,没法晒了。
后来连种也没法种了。白薯一般是秋天收,在白薯井里过冬后,春天出来卖个好价钱。由于灰场渗水,2001年后的五六年,白薯井一度变成水井,白薯只能一收秋就贱卖,来年干脆不少种或不种。
作为忍耐力极强的中国农民,甘雨沟人对渗水和飞灰的回应一度只有几句抱怨。按张树民的说法,谁让自己生在穷山沟,住在低洼处,如果有钱搬出去就不用遭这个罪。
直到2005年,甘雨沟村民决心维权,告别住危房、吃飞灰的日子。那年春节,村民们聚在一起闲聊时,有人提议应该索赔。
春节刚过,十来个村民首次结队前往陡河发电厂讨说法,没有结果。第二次,第三次,村民们前所未有地齐心协力,反复上门。张树民说,直到第四次才得知,自1995年起,村干部每年从陡河发电厂领取一笔数额不等的补偿款,直到2005年,以扶贫、灰场维修等名目总共拿了90多万元。
多年来被蒙在鼓里的村民们去找村干部问究竟,对方不给解释,只让村民们统一口径,要求发电厂出资整体移民。
从村干部那里拿不回钱,甘雨沟人重新把矛头对准陡河发电站。
索赔
造访发电厂的村民越来越多,情况最严重的2007年,平均两三天就有一次,少则几十人,多则三四百人
成群结队地造访陡河发电厂,甘雨沟人不是最早的。负责电厂保卫工作的武警干部林永奎说,2004年就有了,人数和频率越来越多,情况最严重的2007年,平均两三天就有一次,全年共有100多回,少则几十人,多则三四百人。
那些日子,典型的中国农民式维权在陡河发电厂不断重演。张树民说,刚开始去,大家愿意坐到电厂会议室,等待,辩理。几次过后,电厂仍不松口,村民们便聚集到厂区大门前,堵在那里不让电厂职工上下班,最长的一次,堵了三天三夜。有的村民甚至带上炉灶,在电厂门前生火做饭。
拿过补偿款的李家峪、宋家峪、韩家哨等村村民,带着类似的诉求,采用类似的方式,也一次又一次地找到陡河发电厂。
每个村都是全民参与,有过让人记忆深刻的举动。
2006年10月份,韩家哨20来名村民站在陡河发电厂,要求解决渗水问题。“毫不夸张地讲,挖个半米深的坑能舀水出来。”该村前任村主任韩泽廷说,当时陡河发电厂没有明确表态,既不担责,也不推脱,20多个村民于是带着炉灶铺盖在电厂安营扎寨,白天堵住厂门口,晚上睡在会议室。大家一连坚守12天,仍无结果。到第13天,韩家哨三四百村民浩浩荡荡涌到电厂,惊得市里的县里的领导都赶过来。当天晚上11点多,政府有关人员和电厂负责人一起前往韩家哨察看渗水情况。
2007年11月份,李家峪村主任侯庆利领着一群村民试图进入厂区,因为被值班武警拦住,侯等人大怒而动手。武警干部林永奎说,值班武警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其中一个手骨受伤。
强闯厂区,并非一两个村的事。韩家哨村民周恩说,有时候一连去几次,电厂接待人员都说领导不在,改日再来,“我们不相信,自然就想进里面看看领导到底在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