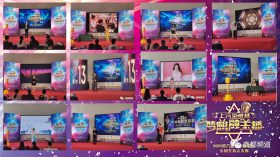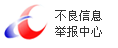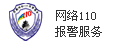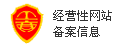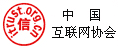我不需要帮忙收残局
10月13日,我和一个供职央媒的本校师兄有一次小小的“摩擦”,或者说摩擦也不算准确,我们生活中没有任何矛盾,甚至还有不少共同的老师和朋友,早前推演几年,我读书时还听过师兄的讲座。看起来倒挺风度的一个人呢。如果有机会相见可能也聊得不错。
文章中我措辞有点不够客气。但由此解释和澄清的一些东西,倒有必要复述如下。客气是属于人情的,观点则需要辨别清楚。
这次事情起因是在郑州大学组织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师兄批评了我近期的报道《“摊派”精神病指标》。我们依托不同的价值和标准来审视同一篇报道。不同是必然的。但师兄提出帮学弟学妹收拾残局,我觉得这个残局不属于我,毕竟是在母校的研讨呢,就对报道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说明。
在中国的公共平台参加辩论游戏,往往会陷身某种乱局,因难有一个标准和原则,大家各自的逻辑出发点完全不同,辩论中又触发新的视角,衍生新的议题。从议题的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来看,好像都有道理。大家各自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难免沦为自说自话的境地。
这种无原则的辩论会导致诡辩和文字游戏,更加不可能有终极的答案,后果是站队和更高一层次的价值观之辩。每个人都挺难过。观点却愈来愈加朦胧。
但仅仅从新闻的专业视角出发的辩论,排除政治和管理者的立场,至少会有一个更能为大多数从业者所认同的标准。这一点倒可依据这篇报道进行说明。我和供职央媒师兄的观点分野,即在对待新闻的不同理解。在此我的报道提供了例子。
郑州“摊派”精神病指标的报道刊发后,出现了一些精神卫生专业内和专业外的讨论。这实属正常,一种现象被报道并置于舆论场中,接受不同观点的检验。为了这组报道,我和我的同事,以及两位可爱的实习生同学到了多个社区,采访病人,社区医生,管理者,还掌握了大量的文件和资料。耗时不可谓不久,以上全部有证据可循。
并且我们当然也看到了一些更大范围的问题——精神卫生的社区服务难题。这组调查报道不能算是完美。但在专业性上,我认为我们坚持了节制叙事的原则。
报道刊发后,我来到郑州,并应约见了郑州市卫生局的多名官员。我甚至当面提出,他们如果对这篇报道的事实部分存在看法,无需避讳。但这些官员并没有当面对这组报道提出任何质疑。
一些继我们之后追踪报道此事的媒体所呈现的操作,显得有点荒诞,比如有的媒体记者采访已经受到污染的信源,称千分之二指标不符合事实,但这是文件上白纸黑字的原话,不知还有何呈现必要。甚至一个视频记者以这样一种方式问郑州市卫生局的一名官员,“为什么媒体会引起误解呢?”
问题在于这名记者在提问前是怎么得出我误解了指标问题的结论呢?他是否向我进行过起码的求证,至不济应该仔细阅读见报的原版报道吧。
在此我们被“坐实”了两点:1,报道强制摊派精神病不专业;2,报道不专业是不了解精神医学。
真的“坐实”了吗?和往常一样,这组报道刊发之后,如果不是这次郑州大学的研讨,我本无意对这些媒体跟踪热点事件时一定会出现的枝蔓进行回应的。
我坚信报道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真实是力量之源。因此全部事实证据均有所呈现,不需解释。而我是事件之外的观察者,不想成为这组报道的辩论方。这是我一以贯之的原则。
我当然不可能了解全部精神医学的知识。但我们的基础调查所掌握的证据材料,和卫计委后来回应时的观点并无二致。郑州市乃至以下各级显然也有自己的难处。这篇报道即呈现了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形。后来各方的回应仅是对它的进一步阐释,并无新意。简单将之解读为一篇批评河南的负面报道,是十分草率的。
我为什么反驳师兄?
一种媒体圈内的批评声音认为,作为一名毕业于郑州大学的学生,不应该报道河南的负面,而应该做一名“建设者”。这种舆论风向经由官员而传导至河南的一些媒体人,竟蔚然成为一种风尚。
我不认为郑大新闻系的学生毕业后报道河南的负面新闻有什么不好,用这种狭隘的地域观念来讨论新闻的价值,本身就相当奇怪的。“建设者”和“破坏者”,是政府官员思考问题的角度,而不该成为一个新闻人替官员思考的问题。
其次外界的一些指责并不牢靠,我们从来没有报道强制摊派精神病指标。我们的编辑不太可能使用“强制”这种概括性很强的字眼。我们的编辑非常专业。为了证明这确实不是我们的报道提到的,我再次阅读了这篇刊发于南都深度周刊,并引发了一些反响的文章,全部接近5000字的篇幅里,没有任何一处提到这两个字。
这是网络媒体转载时的高度概括。我们在见报文章中使用的表述是,“摊派”,“下达”,“层层下发的指标”。我们本来是不需要对这两个字负责的。郑州市卫生局接近凌晨发通告,否认强制,称是“指导性”指标。这种表述是报道刊发后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回应。我更进一步理解,它的回应不是针对报道此事的南都,而是针对“有媒体”。
投射到舆论场中,并不会有几个人区分清楚,这倒也不十分重要。但即使“强制”真的是我们的报道,实际上也仅仅是在表达程度的不同而已,我们仅是因为选择更节制的处理方式,以使自己更专业而已。
“指导性”这样的词语此前并未出现在下发的文件中。这个指标即使被强调在考核中只占“很小很小的一部分”,重性精神病检出率也是记入考核的,考核是与经费挂钩的。基层医生也感受到了上级传导过来的压力。郑州市卫生局这个公开解释在逻辑上和工作流程上显然是不成立的,摊派、包括带有一定量化考核、对工作人员施加的一些行政压力,这是存在的。
另外一种声音认为,郑州此举是贯彻上级的要求,不应受到指责,记者调查不够细致。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原卫生部下发的一个文件,这在报道中有很明显的3段文字进行描述,导语中也有提及。但我们在稿子中同时强调,卫生部的指标,扣分考核是针对省一级的。层层下发到社区,显然是工作方式过于机械才导致出现这个“看起来荒诞”的局面。
郑州市卫生局的一名副局长向我坦承存在这个问题。凑巧,这组报道赶上了一年一次的“世界精神卫生日”,有论者(黄雪涛)称,“摊派”精神病指标引起社会热议,与官定主题的相关程度,比起大多数精神卫生行业的造势宣传,更切合主题。虽然这肯定是卫计委始料未及的——作为报道者我们也始料未及,但也说明了“精神卫生”议题的社会化转型已超出行业及其主管的期望。
由此看来,我没感觉对我个人而言,因为业务操作上的“失误”,有什么残局需要收拾。从主管官员的尺度看,倒仿佛真的出现了一种不同的局面。但谁敢保证这不是一个新的局面呢?
抛开个案,在媒体的洗地行为中,出现的几种类型,技巧高低不一。一种是个别媒体出于地域观念而主动为当地官员所谓“辟谣”,殊不知越辟越谣。另一种是媒体操作手法不够专业,表述方式不够节制客观所导致的意外“洗地”。
官媒关系,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尤其是央媒驻地记者和地方的关系。在一个更大的范围看,地方需借助媒体的宣传,完成任务。记者则需维护和地方良好的关系。
师兄不是我上述所提及的“洗地”行为的代表对象。师兄在演讲中提到了收拾残局的概念触发了我的思考。
这可能出于一种被不断提起的逻辑:站在高处看问题和建设性。这当然和媒体属性有关。但这种看待媒体监督的表述方式,和精神卫生社区服务所面临的困局,有同样的一种逻辑存在——家长式的思维。一些并不从属于新闻而从属于官员的思考被带入其中。可是,谁来规范这种关系中那个看不见的界限呢?
显然,新闻操作技术没这么复杂,总结起来就是真实、中立、理性、客观。尽管有论者在反对理中客,但仅仅从记者实操的角度出发,还真得坚持这个东西。不然干这行就没什么价值了。观点市场的,交给观点市场。其他的,也交给其他吧。
当然,并没有恒定的价值判断。从另一个尺度看,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真相,纷纭难辨的只是你我他的不同语词游戏。我以上所谈的这些也都全不重要。
作者:王世宇